庄宇默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国内围绕社会底层问题的政治辩论经常与族群问题纠缠在一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异军突起,其设置的一个重要议题即是所谓“底层黑人”问题,认为聚居于城市中心的底层黑人深受文化左翼的权利平等运动的影响,过度依赖社会福利救济,沉溺于缺乏责任感的社会文化之中,形成了底层黑人社区的恶性循环。这一叙述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这种恶性循环是否只是底层黑人特有的?追求平等与过度的社会福利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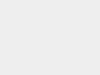
2016年美国大选前后风行一时的《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刘晓同、庄逸抒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指出,美国铁锈地带白人工人阶级的状况与底层黑人群体的状况非常接近,白人工人阶级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最悲观的群体。作者J.D.万斯三十出头,少年时期在绝望感弥漫的社区氛围中挣扎,后来通过加入海军陆战队的历练,考入耶鲁大学法学院,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他以亲身经历描述了穷人们的濒临绝望,以及美国制造业在后全球化时代日益衰落的背景。
这本书被认为揭示了特朗普崛起和当选美国总统的社会动力,通过它可以“读懂特朗普为什么能赢”。书中重点强调的铁锈地带白人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即是特朗普在铁锈地带获得竞选优势的基础所在。在一二十年前的政治辩论中,新保守主义的成功之处在于调动了南方白人平民的不满,但主要方法是强调保护少数族裔的政策造成了对白人的“反向歧视”,白人平民认为自身利益受损,少数族裔受到过多照顾。现在更多被强调的是,美国工业竞争力下降与移民对白人工人工作机会的严重影响,这是特朗普相对于里根和布什父子时代的新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变化。
《乡下人的悲歌》清晰地呈现了这一中心议题的变化。以往所谓底层黑人社区的文化问题,不再只被认为是黑人族裔的特征,白人工人阶级同样有这一特点。万斯指出,白人工人阶级中形成了一场把责任推给社会或政府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至今仍有追随者。同时他又进一步给出了强调族群区隔的解释,认为他自己属于苏格兰—爱尔兰人后裔中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数百万白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与东北部信奉新教的盎格鲁—萨克逊裔白人有所不同,前者被称为“乡下人”。
也就是说,美国底层社会问题不能简单等同于底层黑人问题。当前80%左右的美国人处于低工资水平,但非洲裔美国人只占人口的15%,显然黑人在美国穷人中仍然只是少数群体,拉美裔同样如此【皮特·特敏(Peter Temin),《消失的中产阶级:二元经济中的偏见与权力》(The Vanishing Middle Class: Prejudice and Power in a Dual Economy), MIT Press, 2017】。此前二三十年美国大选的政治议题一直纠缠于底层黑人社区秩序问题(以及堕胎、同性恋等问题),未必不是城中心底层社区失序现象向城郊蔓延的一大原因。
万斯在书中多次提到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的《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成伯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分析了底层黑人社区面临的社会问题,克林顿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时曾推荐过这本1987年初版的书。而他之后就任总统的布什则推荐了麦隆·马格尼的《梦想与梦魇——六十年代给下层阶级留下的遗产》,此书开篇即展开对《真正的穷人》的批判,认为民主党的各种社会政策给人们提供的保障纵容了犯罪,使底层阶级对失业无所谓,也使得非婚生育和单亲妈妈家庭越来越多,所有这些都发展成一种贫困文化和福利文化。这些思想交锋的议题主要围绕底层黑人社区展开。
万斯在一定意义上综合了上述两派的看法,一方面认为“真正的穷人”是真实的存在,而且包括白人工人阶级,另一方面认为穷人社区的确陷入了悲观绝望与依赖社会福利相互叠加的恶性循环,形成了缺乏责任感的社区文化,无论何种族裔的穷人社区都是如此。
这是所谓“1%富人与99%穷人”的剧烈分化格局之下的现象。不过万斯无意于追问如何应对或改变这一社会格局,他的兴趣在于如何改变贫困社区的文化习惯,以及个人如何从绝望的社区氛围中走出来。他以自己的经历,呈现了部分家庭成员保护少儿获得学习机遇和兴趣的重要性,海军陆战队的成人训练,以及个人努力和选择的重要性。在严重失衡的社会中,这种个人努力是有效的,也是偶然的和极为有限的。万斯以其坦诚,生动揭示了当前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以及将反思视野局限于穷人阶层的无力。(编辑 董明洁 许望)
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
 分享成功
分享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