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对今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水形物语》似乎有着两种颇为相反的观感。赞赏者赞其奇幻有内涵,视其为导演托罗为弱小者谱写的童话;厌恶者厌其“人兽恋”的荒诞不经与女主角的“不够纯洁”,认为这种童话陈旧而虚假。这两种观点可以说都有其合理的地方。因此《水形物语》的获奖,除了体现了奥斯卡对“政治正确”的沉迷以外,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天的我们还需不需要童话?或者说,这种童话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才能让我们再一次相信它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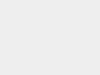
《水形物语》中的隐喻是很明显的。哑女艾丽莎、失业画家吉尔斯、黑人女清洁工泽尔达、被政府擒来做实验的人鱼……这些都是社会边缘人士或“异类”的代表。他们虽然存在着,却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主流社会对他们的轻蔑与压迫。在孤儿院长大的哑女,自小习惯了被忽视的命运,学会了从细微处享受生命的欢愉,也练就了内心的强大。清洁女工泽尔达做着底层工作,守着好吃懒做、懦弱无能的丈夫,在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迫下,她坚强乐观、乐于助人的天性只能在最有限的范围内散发光芒;片中她与艾丽莎的友情,透露出一种被轻蔑者之间的惺惺相惜与互相扶持。画家与泽尔达都不是聋哑者而能够懂得哑女艾丽莎的语言,这一情节设置显示了语言从来都不是交流的障碍,而被忽视与被侮辱者之间的联结有一种精神与意志力的内涵。
与他们形成对比的是主流与成功者的社会,《水形物语》为此提供了两个富有意识形态意蕴的例子——“冷战”背景下的美国与苏联。上个世纪60、7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霸权而在科研探索上展开激烈竞争,当发现探索的对象没有价值时,则毫不留情地将其抛弃。片中的美国是一个天空灰暗、没有阳光的国度,所有的色彩都有一种凝固的暗沉,仿佛浸染了时代的阴云。唯一闪亮的色彩是人鱼身上的蓝绿花纹;而当人鱼为艾丽莎所动时,其身上闪耀的光点,更像是导演对爱与美好的直观写照——爱能够引起心灵激荡,爱也将点亮一个人的生命。
当艾丽莎听到研究所将对人鱼进行活体解剖时,她决定救出人鱼。这与其说是出自对人鱼的爱恋,不如说是出自对人鱼的同情及他们之间的心意相通——她对这一被囚禁的奇异生物有着天然的同情与好奇,而人鱼与她的沟通,则令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被认同的快乐。她对画家说:“他看我是完整的”,这句话透露了她所生活的社会是如何一直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她的。她对人鱼所产生的亲切与共鸣,正代表着她在这个社会中得不到的东西。
影片将这个社会的主流表现得冷酷无情。当被擒获的奇异生物失去研究价值时,他们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将其活体解剖,而不是放回其所属的大自然。这种唯我独尊、对其他物种毫无顾惜之情的态度,正是主流社会对边缘与“异类”人群态度的写照。
导演借研究所保安主管理查森这个人物描摹了这种价值观的冷酷性。在权威、利益与所谓“成功”的驯化下,理查森是一个残忍、无耻却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他心知肚明,这个以“成功”为标准的社会,是不允许失败者存在的——一旦失败,就要出局。这也使得他愈加残忍地对待他人,对待自己。
当人鱼被劫走以后,将军威胁他:“如果36小时之内找不回人鱼,你在上流社会就不复存在了。”然而此时他藉以鼓励自己的竟是《如何正向思维》的励志书。当将军斥责他凭什么有信心能找回人鱼时,他答非所问地答道:“我不能有负面思想”——这稍纵即逝的一笔,饱含着导演对现代社会种种“驯化术”“自我安慰术”的讽刺。
作为意识形态的另一端,苏联也是如此。作为间谍的科学家再无利用价值以后,“消灭他”就成了无需犹豫的选择。片中身为苏联间谍的科学家,奉命窃取实验成果和杀死人鱼,然而在人鱼身上并没有发现所谓“生物武器”的秘密之后,他选择帮助艾丽莎放走人鱼。这是他作为一名科学家、在知道人鱼并不会对人类造成危害后所作出的选择,其背后的价值观是生命可贵、万物平等。然而这种科学主义的价值观并不为苏联所容。
艾丽莎爱上了人鱼;她的底层朋友帮助她救出了人鱼;人鱼和艾丽莎一起快乐地生活在水中世界。这一底层与弱小反抗庞大与主流的故事,可以说是一则当今世界“政治正确”的寓言。这一寓言虽然美好,却因为电影的设计感与主观意图太强,而显示出一种难以寄托的虚无。因为虽然人人向往正义美好的世界,现实的难题却不是寓言与童话般的美好构造所能解决的。(编辑 董明洁 许望)
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
 分享成功
分享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