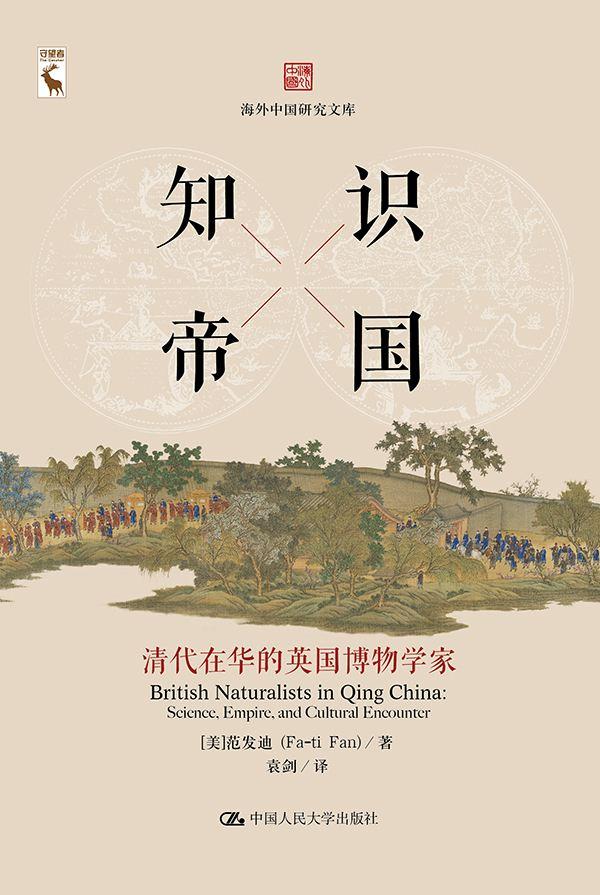陈华文
近三百多年来,伴随全球工业革命、资本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整个世界向现代化转型。但是,世界进程并非齐步走,而是极为不均衡。尤其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开辟海外的贸易市场,以殖民主义加速了世界贫富的分化。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国门被迫向英国打开,心怀不同目标的英国人深入中国各地,从事形形色色的活动。这些英国人当中,就有一些博物学家,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采集动植物标本、从事田野考察。可惜这些历史往事,在当代中国已经鲜为人知。《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对于从他者的维度解读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新视角。
本书作者范发迪(Fa-ti Fan)主攻科学史、环境史和东亚史,1999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学位,现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担任副教授。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他另辟蹊径,在参考大量学术文献的基础上,从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这个独特的视野,探索近代中国别样的历史叙事,令人耳目一新。全书分为“口岸”和“地域”两个部分,由“中国商埠中国的博物学”“艺术、商贸和博物学”“科学与非正式帝国”“汉学与博物学”“内地的旅行与实地考察”五个章节构成。
博物学是19世纪在华欧洲人最广泛的科学活动,本书即从文化遭遇的观点去检视博物学史,从博物学的视角剖析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流和碰撞,并特别关注文化遭遇下的知识传统和文化霸权问题,从一个全新的“切口”揭示了近代中国在知识领域的顿挫与转折,为学界研究中国近代知识转型开辟了新路径。
《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一书中,在对博物学家进行群体“画像”的同时,也深刻分析了科学、文化、政治、地理之间的紧密关联。阅读这本书不难看出:推动世界发展进程的,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实在英国博物学家们抵达中国之前,在西方世界的著作中,就流传着有关中国繁华城市和奇花异草的各种传说。不仅在文本记录中,还在中国瓷器及各种工艺品的图案造型中,独有的草木飞禽,吸引英国博物学家来华考察和探险。
深入中国各地的博物学家们,其实也没有几个是职业性的专家,很多人的身份是使节、商人、传教士、船员等等。当时由于交通运输的不便,对于他们而言,只能把注意力放在植物学标本的采集中,本书记录了他们在中国各地采集植物学标本的经历。这些博物学家们,最远的抵达西北、东北,但多数集中在西南、华中、江南等地。博物学们以乘船、坐轿、骑马、步行等方式,来到了内地。英国人黄头发、白皮肤、高鼻梁、蓝眼睛的相貌,引起中国人的好奇。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大量的中国人看热闹。起初,英国博物学家们颇不适应,这在他们的礼仪和价值观中,显然是不礼貌和没有教养的表现。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这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人的表现其实和教养无关。
英国博物学家在华进行植物学考察活动时,最感兴趣的内容之一是研究茶树。道理其实很简单,这和英国人也爱喝茶的习惯有关。其中一名叫福钧的英国人,在中国茶区的考察过程中,对于平息一场为时已久的有关不同茶叶种类的争论起到了作用。欧洲博物学家长久以来对红茶和绿茶是否属于相同的茶树很困惑,而在考察中他惊讶地发现,中国人极为富有智慧,能把同一棵树上采来的叶子,分制成红茶和绿茶。红茶和绿茶,有的只是不同的栽培品种,而非两种不同的茶树。
晚清时代,英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大批来到中国内地,而博物学家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群体。主观上讲,博物学家到中国腹地,目标只是科学研究。客观上讲,这也算是外国人主动探究中国“家底”,从战略上来看,对中国构成了潜在的安全威胁,这一点毋庸置疑。从表现上讲,这些英国博物学家看上去满腹经纶、彬彬有礼,颇有绅士风度,而本质上,他们与西方殖民者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
清代的中国,尤其是晚清时代,整个中华大地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正是因为晚清当局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成群结队的西方人才得以有条件进入中国腹地。当时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们,尽管对待中国都具有居高临下的优越之感,可是他们内心也都意识到,中国这头沉睡的东方雄狮,哪一天一旦醒来,世界都会为之瞩目。晚清的中国,和当下的中国今非昔比,无论世界如何变幻,那个不堪历史重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编辑 董明洁 许望)
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
 分享成功
分享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