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再思考
十年前,正值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之际,一位非常资深的媒体朋友问我:在近似的大时代背景下,明治维新为什么能够成功,而中国的百日维新下场竟如此悲催?确实,日本那似乎莫名的发迹,究竟肇端于什么样的殊途,这当然是个耐人寻味的好问题。
十年来,带着这个问题读了不少关于日本现代化历程的经典著作,但直到读过马国川先生的《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一书后,才终于觉得有了能让人迅速在这个问题上豁然开朗的读物。
与清末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一样,自从日本被美国舰队打开国门之后,“日本向何处去”就成为当时许多忧国之士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国家的启蒙》没有陷入宏大叙事的俗套,而是循此追根溯源,将对日本近代化产生重大作用的近40位历史人物和若干标志性事件作了一个全景式的描绘和梳理。这本书既是手卷,又是白描,在个体毕生的追问、探求、抗争、反思中展开的是影响国家命运的思想激荡。如此,跟着马国川先生的笔迹在历史的情境中追问“日本做对了什么”,答案自然呼之欲出——那就是当时涌现了一大批推动日本现代化的英雄们,他们的眼界和价值观的演变、进化带动了整个国家思想的转型、进步。
书中渐次展示给我们的真相是:在这种大变局时代,推动社会进步的真正的思想力量来自民间,且多为低级武士。
公认的日本改革设计者坂本龙马写出《船中八策》和《新政府纲领八策》时只有32岁。此人基本是以民间志士的身份在游历,但却奠定了明治维新的理论基础,成全了日本新国家体制的“顶层设计”。新岛襄本是一个下级武士,但受《鲁滨逊漂流记》的感染,辗转到美国成为第一个读了西式大学的日本人,31岁回到日本后创办了同志社大学,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所基督教大学,这所大学以“培育自由和良心的人们”为己任,培养了大量人才并直接促进了日本的“文明开化”政策。而作为日本近代之父、庆应义塾创办者的福泽谕吉,在长达十二三年的时间里,专心从事写作和翻译工作,全面介绍西方发达国家的地理、兵法、科技、航海等知识,创办了《产经新闻》的前身《时事新报》,并通过出版一系列文章提倡自由平等的进步思想,身后留下一所大学和22卷文集。这些来自底层或边缘的民间社会精英,他们的思想比当时身居高位的人更持久,更能穿透历史和影响一个国家的兴衰。
纵观全书,不难发现,这些开风气之先的英雄们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投身于兴办教育。这表面上看是当时日本整个社会注重教育的结果,但很大程度上却是韦伯的新教伦理的日本版本。
与福泽谕吉共同倡导新价值观的另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中村正直,他翻译的斯迈尔斯经典著作《自助论》在日本狂销百万册,这本书恰逢其时地对当时日本中等阶层的职业伦理带来深刻的促进作用。《国家的启蒙》中引述了《日本文学大辞典》对中村正直的评价:“如果说福泽谕吉使明治青年看到了‘智’的世界,那么中村正直则让人们看到了‘德’的世界。”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这样评价这种价值观教育的作用:“在一个没有正规的宗教教育和礼仪的国家里,学校成了道德品质和伦理教育的殿堂。”而“有了这样的职业道德,所谓的日本经济奇迹才成为可能。要认真理解日本的成就,就必须看到这种由文化因素所决定的人力资本”。
新的文化因素和人力资本孕育在最具活力的人身上,这种代际之间的新陈代谢也是日本成功变革的原因之一。“少年强则国强”,当时的日本相对僵化、封闭、保守,年轻人能够脱颖而出、主导变革也是日本在价值观层面能够成功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来自于基本的思维方式。伯纳德·刘易斯说过,当人们认识到出了错误时,他们可能提出两种问题,一种是问“我们做错了什么”,另一种是问“这是什么人搞的”。前者会引发关于我们如何纠正的思索,而后者会导致阴谋论和偏执狂。日本在19世纪后半期正是按照前者的思路逐步改革开放,走向繁荣富强的崛起之路。
当然,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伦理建构有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最终以德国为榜样,踏入军国主义的泥潭。历史学家钱乘旦教授曾评价,明治时代的日本将西方文明中不符合国情的若干重要部分剔除,而这些很可能就是西方文明中的精髓所在。所以,日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虽然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清政府走得远,但终究由于狭隘和短视而功亏一篑。在付出几乎亡国的惨痛代价后,这些问题在日本二战战败后才逐步彻底解决。(编辑 董明洁 许望)
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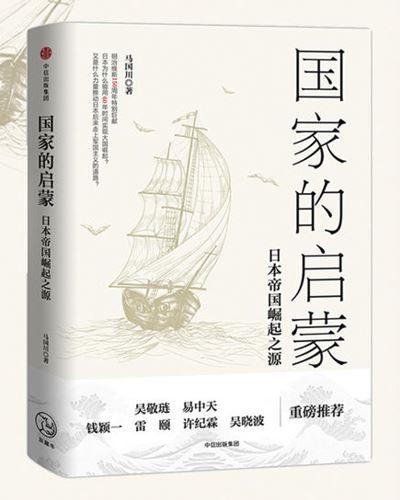
 加载全文
加载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