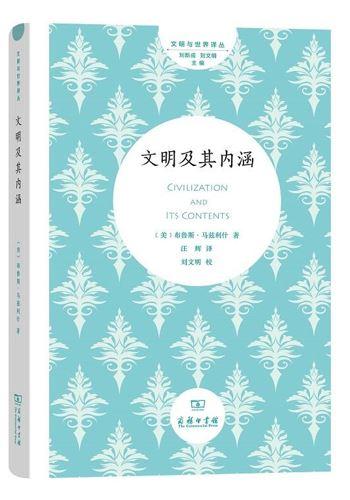解构文明
庄宇默(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文明论并不是真理,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十九世纪才开始随着西方列强的全球扩张流行于世界。美国学者布鲁斯·马兹利什的《文明及其内涵》(汪辉译,刘文明校,商务印书馆,2017年)通过梳理“文明”的概念史,指出文明概念是社会建构而成的。他认为,在我们自己选择并称之为文明的东西中,既找不到“本质的”、也找不到“天然的”特性;我们可以赋予它一种本质或者本性,但这一行动就是一种社会建构的形式。斯宾格勒、汤因比或亨廷顿或多或少将各个文明当作固定和封闭的实体,几乎不向外开放,也不与其他文明相互借鉴或者产生联系。
根据马兹利什的梳理,文明概念的建构时间与民族国家在欧洲被确立为社会联系的主要形式的时间大致相同,也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形成的时间大致相同,都在十八世纪末期。马兹利什的这些研究有其基础,例如法国思想家福柯在其名著《词与物:人文学科的考古学》(修订译本,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中曾分析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形成。法国大革命改变了社会正当性的基础,民族国家取代以往的宗教成为最高主权的象征,成为终极价值的来源,从此社会开始从超验走向世俗,个人也从他律走向自律。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在思想上打破超验与他律的限制,这种哥白尼式的革命为现代人文社会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现的新政体提供了知识上的保障。
文明及其内涵。资料图
马兹利什指出,必须把文明概念的兴起放到社会科学兴起的大背景中理解,它标志着自我反思意识的出现,这种意识认为它知道集体如何发展其应有的规范。这种意识的形成与欧洲在全球的扩张有关,欧洲人与新大陆及此后太平洋诸岛上的“原始人”的相遇激起一个疑问,与“野蛮”相对的“文明”的人是如何形成的?文明概念最初既体现了一种欧洲中心的视角,同时又体现为一种放诸四海皆准的衡量尺度。到19世纪初,文明概念作为一种殖民意识形态,越来越带有种族主义的特点,“欧洲的自我认知中掺入了一种恶毒的种族主义。”马兹利什认为,在殖民时代的欧洲,文明与野蛮的二分法变为一种越来越充满恶意的欧洲意识形态,文明只可能是欧洲人独占的产业。
在马兹利什看来,文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建构,通过区别于外在的野蛮人,来赋予自身社会的特征,这种情况将持续下去。通过对文明概念的解构,他试图把此一概念拉下神坛,文明作为一个有用的概念已经接近尽头。同时他又认为,需要重视“文明”概念所指的作为“过程”的内涵,即个人、国家和所有人类走向教化的过程,“文明化进程(civilizing process)”应该留下来,应当调转方向重归“文明化”。
马兹利什对文明概念的解构式梳理,对分析当前的文明论提供了一些启发。从这个角度说,不能简单地将文明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首先需要将文明论作为社会科学分析的对象。
(编辑:董明洁,许望)
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