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从起家时的ToB平台到后来成为消费者平台,苹果从卖硬件的公司变成卖内容和服务的,而刚刚在上交所递交招股书的京东数科也是如此——从ToC的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逐步进化成一家ToB的数字科技公司,用技术去服务全行业。

好公司不是一步养成的,许多都经过数次迭代。而在京东数科看似不相关的三大战略迭代中,一个基本逻辑并没有变——用数字和技术不仅服务金融,也服务全社会。
1、2013~2015初创:做数字金融
2013年10月,京东上市的事情大局已定,刘强东开始想着扩展业务,做金融。他的逻辑很清楚——包括沃尔玛、 GE这些大公司很大一块收益来自于供应链金融,而京东本身有大量的供应链,在金融上必然有机会。
于是,在高管会上他提要做金融,问谁愿意。有人举了手,但刘强东心里看准的那个人没有举手。他看好的是他的CFO陈生强,但当时这位老臣一心打算的是退休,回福建老家养老。
因为心里窝囊。京东上市之前的工作一直是陈生强筹备的,到了工作完成得差不多的时候,刘强东空降了一个联席CFO——美国上市,但陈生强没有上市经验。“于理”能够理解,“于情”心里过不去那关。反正对刘强东已经有了交代,陈生强打算就此离开。
刘强东看上去风轻云淡,但心里打定了主意不会让他走,他要把金融的新摊子交给陈生强。刘强东找准一切机会和陈生强描绘新业务摊子,不管是在在北京,还是在纽约出差途中,甚至也发动身边的人去做说客。陈生强在财务部,和刘强东的助理缪晓虹所在的总裁办办公室挨着,两人关系非常好,缪晓虹就成了刘强东的“使者”,三天两头去找陈生强聊天,劝他留下,接新业务。
他决定去看一看。他带着团队,从北京飞到旧金山,从旧金山到纽约,短短一周内拜访了二十多家公司,回来回复刘强东,“让我做京东金融,我希望能做成一家能够长久的,必须是跟京东一样伟大的一个公司,否则我就不做了,”他的意思在于,他对于公司有自己的意志。这与刘强东需要的正是他这样的决心。
随即,京东金融在集团内部成立。陈生强带着原先财务部做供应链金融和数据的二十几个人,在北京北四环北辰世纪大厦租了一个200平米的办公室,加上在另一栋大厦办公的京东网银在线的70个人,不到100人开始了创业。
商城上下游大量应收付账款需求早已积累,供应链金融业务水到渠成,一如刘强东所设想的那样。
与此同时,京东也注意到消费者业务——商城每天收到大量信用卡申请不下来、额度不够用甚至是希望分期的用户留言。京东金融副总裁许凌回忆说,当时如果真正要跨入消费者业务,还是底气不足,“友商”支付宝已经成立了十年,有深厚的用户基础,“在支付上硬碰硬没有胜算,必须换道。”
换一个赛道,京东想做信用产品。
一开始想的是和银行合作。加入京东金融之前,许凌在工行做风控,做出过影响全国的风控模型。于是,他去告诉老东家,京东可以提供风控模型、用户流量,银行只需要对接资金;银行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京东金融推荐的客户在银行网站填申请表,三天内用户去银行线下网点提交收入证明。“所有的流程都没变,只是把我们当导流入口,我觉得这个事儿价值不大。”许凌说。
那就只好用京东自己的真金白银上,团队想到“赊销”模式——用户在京东消费时,由京东提供相应的延后付款或分期付款的付款方式。在2013年初期,市场上就传出阿里要推出一款消费金融产品,因此留给京东金融的时间窗口非常小。许凌团队开始2013年11月团队把这个“白条”产品原型写出来,12月份就开始内测,最终由刘强东亲自拍板,在2014年情人节上线。
上线即爆款。由于当时支付宝的“花呗”还未推出,白条增速飞快。2014年年“6·18”,白条更是让集团看到了价值——白条客户的客单价比非白条用户客单价高一倍。
从商城业务到数字金融业务,京东横向扩张这一步走对了。
白条很快引起了银行的警惕和关注——一些银行关闭了信用卡还款白条的通道,而一些银行却看到了合作的潜力。中信银行就是后者,2014年,双方花半年打通了系统、用户、风控模型。在白条第一张联名的“中信小白卡”发行100天内突破了100万张的申请纪录,效率比传统渠道高出10倍以上。一位股份制银行的高层曾透露:传统银行信用卡获客成本大概在100~300元左右,跟京东金融合作,成本可以降至一半,而且不良率非常低。

银行和互联网之间的对立在彼时已初现雏形——支付宝结算收单能够绕靠银联,京东自己发布信用产品,尤其是当时火爆的P2P产品颠覆银行以往的信用审核的权力……大家把这些产品叫做互联网金融。P2P最红火的阶段,是否要涉水这一业务,京东金融内部也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讨论。讨论的结果很明确:不做,因为对京东没有任何价值。
陈生强并不喜欢互联网和传统金融的对立。有次在五道口上课,班上同学请陈生强谈一谈互联网金融, “我从来不觉得应该要有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一提出来就意味着你要跟传统金融是对抗的,我不认同这个观点,”他说。
他想的是合作和服务。随着京东用数据帮助越来越多的银行降低成本、降低坏账率,用数字解决了对方的问题,这回到了他的基本逻辑上——数字解决业务问题,他看到了更大的机会。
尽管金融做得很好,但是陈生强不满足,开始想变革。
2、2015~2018变奏:反”主”为”客“,用技术服务于金融
陈生强的“用数字解决业务问题”的基本逻辑在创立经分会的时候就展示出来了。
时间拨回到2010年。在那以前,京东订单执行慢了,用户体验不好,就是不断加人加仓。陈生强觉得这不对,他抽出人手去到第一线去观察细节。比如,某打包员一天打了多少包,每包的货量和体积,这个人习惯把箱子竖着还是横着,打包时候站着还是坐着,缠胶带几圈,是什么方向缠的……陈生强把这些细节统计出来,找到效率最高的模型,然后规定每个库管必须照模子抄。不仅仅是仓库,陈生强把所有关键点都数字化,找到最佳实践,这就是经分会。2011年京东人头只增加了20%,历年最低。经营分析会体系的建立,将京东的决策流程数字化、规范化。接手京东金融之前,陈生强每三个月给经分会加减指标。
他想回到这个基本逻辑上,让京东金融换一个落脚点。到了2015年第三季度,陈生强提出要成立一个专门的金融科技部门。
换条路走并不容易,内部首先要取得共识,有人质疑他,“许多金融牌照也有了,用户也有了,钱也舒服赚着,为什么要换赛道?”有的人直接离职。
陈生强游说公司的管理层,“其实我们做的事情,本质还是以金融为核心,只不过是更多的以技术为手段。基于这个逻辑,我们就定位为金融科技公司“。那个时候市场上没有人做金融科技,现在看来,如果顺着互联网金融一条路走下去,势必与支付宝直面竞争,跃身于红海。
整个说服过程长达9个月,到了2016年9月,京东金融正式成立金融科技事业部,开始在京东金融九大业务条线之外,明确独立部门进行科技能力输出。
京东金融服务的市场很明显,举个例子,一个简单的银行存款证明服务,对银行而言,通常用户来了就办,办完就走。但如果去挖掘背后数据,比如用户使用存款证明是旅游还是留学场景,让用户得到细分,能够进一步挖掘用户的外汇需求或者出口退税需求,从而带来服务的差异化和用户粘性。事实上,大量的区域性银行科技部门通常只有一二十个人,连维护系统的正常运行都不够,更难有余地开发更多新产品。京东金融可以帮他们专业做这些事情,提供数据分析,提供解决方案。
逐渐的,京东金融逐渐推出了资管理财平台系统、保险基金网上代销平台、资产证券化云平台等数字化系统或工具,为银行、资管、保险、证券等各细分金融行业提供全产业链数字化解决方案。
当时的业务发展也顺利。到了2017年第二季度,京东金融从京东体系剥离,成为独立的公司。当年,京东金融净收入超过100亿;到了2018年第三季度,京东金融实现全面盈利。而从2017年随着P2P暴雷开始,互联网金融受到了极大的监管——陈生强为京东金融的路选对了。
资本市场也认可这条路,频频入股。
2016年1月,京东金融获得包括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嘉实投资等机构投资者66.5亿元的融资,彼时估值达到466亿元人民币;2018年7月,京东完成B轮融资130亿元人民币融资,投后估值约1330亿人民币。
当时外界将京东金融横向对比的都是蚂蚁金服、陆金所等互联网金融公司,但实际上,陈生强又在想下一步变革。
“金融业务是我们的收入和利润的重要来源和支撑,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才敢也才有资源投入到新业务中,也才能做更长期的规划和布局“,迭代没有出现收入断崖,陈生强开始了新的折腾。
3、2018~亮出野心:服务全行业
在服务金融行业时,陈生强已经抓住了技术这把利剑,他的野心在于,既然服务于金融行业这个商业模式能够走通,那也能够服务于其它行业,甚至服务整个城市。
2018年9月,陈生强正式亮出了自己的野心,京东金融更名为京东数科,京东金融成了京东数字科技旗下的子品牌。公司到了第五年大张旗鼓地改了名字,他需要向所有人解释数科的道路选择。“并不是说我们放弃做金融业务了,而是我们基于数字应用边界的拓展,业务范围早已超出了金融行业本身,所以我们决定使用一个新的定位和新的品牌来诠释公司的变化。”
陈生强在当时对内部的演讲中表示,”我们的金融业务和非金融业务是什么关系?金融业务原来是独生子,现在有了二胎三胎。“如果说京东金融业务在五年前成立,是由零售业务向金融业务一次扩张,而技术则是陈生强早就看准的一条道路,在金融实践中抓住的,这一次是服务金融之后的再一次横向扩张。
但逻辑没有变,用数字和技术服务金融那一套扩展到养猪养牛,就是京东农牧,扩展到媒体就是京东钼媒,但如果用数字来服务整个城市的运转,这个想法如何?

此前还只有IBM这样的外企提“智慧城市”的概念,广告打得到处是,但在中国难以落地。陈生强想得远,数科也要做智能城市, “核心是打通城市的数据,同时开始做一些新的技术储备。”
陈生强在一次行业论坛上见了在微软做城市计算的郑宇,就去挖郑宇了。郑宇2007年毕业从成都到北京,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研究环境宽松,但北京居住环境让他不爽。他从堵车开始做,从微软的必应的地图里抓出出租车数据,优化行车路线,能节省20%的时间。然后再一步一步扩展到更多领域,比如污染。
几年间,计算机领域很多热门的课题兴起,比如大数据和AI,但郑宇都没有挪窝。坚持八年的结果就是,郑宇提出了“城市计算”这个概念,成了学科带头人,获得了MIT的奖,现在美国有大学开了城市计算的硕士学位,用的是郑宇写的教材。2014年入选《财富》40个40岁以下商业精英——他懂技术也懂商业。
但城市计算商业化太特殊,必须和政府打交道。有好几年郑宇跟着微软中国的销售去接触官员们,为了打一个环保部的单子,做300多个城市的空气分析和预测,而环保部有自己研究机构,关系到国计民生,微软又是外企,很难。 做研究的没有不想自己成果落地的,他被陈生强说服,加入了京东数科,担任智能城市业务板块负责人。他不再把自己定位为科学家,而是技术行业的变革者,“既然要做革新者,就要实现全链路的闭环,从研发、技术到产品,最后落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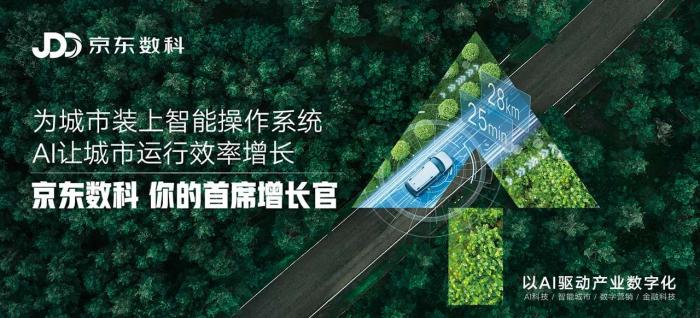
智能城市业务在京东数科迅猛发展,包括在雄安这样的白纸一张的城市上,完全落实他的构想。 在2019年,雄安政府宣布,京东为雄安打造了“块数据平台”。这个平台上会搜集城市各个节点的数据,勾勒整个城市的活动轨迹,然后融合这些数据,形成解决方案。在雄安政府的规划中,政务数据未来会和市场和社会数据有效沟通;这个平台会横切进政府所有的管理系统,政府在这个平台上运作,最后,再一个保证数据标准化,保证数据可流动,平台可持续。
不仅仅是雄安,在江苏南通、在北京亦庄、在王府井大街,郑宇和陈生强的智能城市想法都得到了落地,从纸上的点子到沁入人们日常生活。
还是那个根本逻辑,数字服务于金融、服务于农牧、服务于媒体、服务于城市,加起来就是京东数科总和,而陈生强是刘强东身边最懂这个逻辑的人。
这样看来,刘强东当年把金融业务交给陈生强并不是为了安慰,而是真正的信任。
从数科的招股书上,京东数科从2018年到2020年上半年收入一直在攀升,……陈生强的第三次战略迭代又成功了。不过,京东数科的迭代并不会因为上市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