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某些原因,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偏极端化的达尔文主义对人类社会影响深远,这种思潮超过了经济学、生物学范畴,不断影响着社会走向,比如十九世纪的无政府主义就源于进化论。近年来,我在做行为经济学研究时,重新思考经济人假设,弗农·史密斯总结的亚当·斯密的完整理论(他称之为Humanomics)给了我启发,我们应该重新理清利己与利他,从而更深入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于何处。《一个利他主义者之死》是乔治·普莱斯的传记,可以帮助我们从理论和历史两条主线上理解利他主义的缘起和发展,其观点发人深思,这是一本有关利他行为研究的生动有趣的科学传记。《超级合作者》则是专注破解“合作”之谜的马丁·诺瓦克团队关于利他的理论阐述,抽出了前一本书的人物故事情节,提纲契领、层次分明地总结了合作的五大机制,并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实例做了进一步引申,阅读这两本书,几乎能解决我们对合作与利他行为的所有疑问。
《一个利他主义者之死》刻画了许多历史人物,其中既有达尔文、赫胥黎这些自然科学家,也有克鲁泡特金、赫尔岑、巴古宁这些政治人物,还有很多跨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第1章和第13章是精华所在,充满了深刻的哲学思辨,有力地论证了互助利他是由动物生存的本能决定的这个正确观点。这本传记不仅描述了一位研究利他主义学者的一生,而且梳理了生物进化遗传理论发展史。而这个本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进展也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社会思潮和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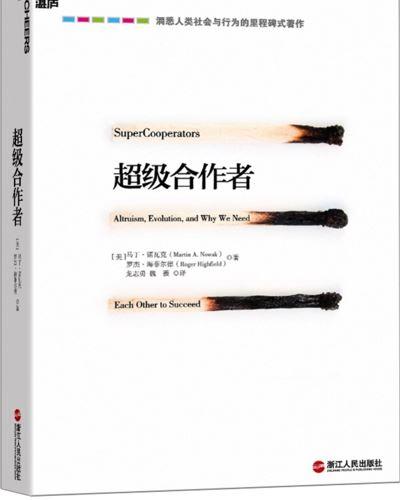
物种进化理论一直强调的是“竞争”,而实际上,无论是在动植物界还是人类社会,“分工合作”都是普遍存在的,比如蚁群、蜂群、某种菌类植物等。充满竞争的自然选择过程并没有让世界变得更混乱,而是衍生出了受到各种规范约束的秩序。我们能观察到的存活下来的种群都有合作和利他的行为,有些甚至是其得以存活的关键原因。自然选择的对象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开始是在个体层面,后来扩大到了群体层面。与恶劣自然环境的竞争,推动了物种间的合作,通过淘汰,我们现在只能观察到具有合作与利他行为特征的生物种群。科学家为此做了很多假设,提出了亲缘和群体选择模型,但都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完整解释,现在倾向于认为这类行为促成了社会基因的形成并能够在代际遗传。
我们从进化生物学研究中得出的生物学上的合作利他行为,与人类社会中表现的合作利他行为并不是一回事,但是从中可以发现来自进化进程的解释。我们很难推断某类只负责服务和看守的蚂蚁具有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但对于人类则不存在困难。与竞争意识相比,合作意识已经成为人类本能,合作利他行为可以从直接互惠和间接互惠角度理解。这是一种社会能力,在一些低等哺乳动物和人类身上,都能看到为了社群福祉而表现出的具有社会本能的行为,最终在竞争和合作利他之间达到了一个均衡态,即在个体间进行有限度竞争,自我克制,以及在群体内进行分工合作。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伦理道德意义上的社会性规范,换言之,分工合作和利他不是道德的产物,而是由生存发展这个首要需求决定的,是这种需求决定了道德的内涵,我们一直都不是在空洞地谈论道德,而是必须身体力行,才能确保种群安全有序地繁衍。至于新生儿是否已经进化到天生具备这种“社会基因”,目前没有定论,但是人类有共情能力,已经能完成伦理道德规范的传承。新生儿来到这个世界之时,就置身于一个伦理道德成型的社群之中,并从中学习和沿袭了利他行为的社会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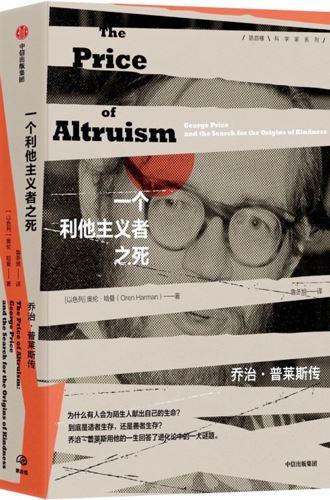
博弈论对于竞争、合作和利他行为也设计了一些博弈模型,解释了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能够既竞争又有合作,既利己也存在利他行为。一个占优策略就是始终保持合作态度,但是碰到对方不合作时予以惩罚。在现实生活中,“囚徒博弈”困境实际很少出现,因为存在很多社会规则,导致支付矩阵上的每个收益损失计算并不简单。人类具有远超低等动物的观察和感知能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凭借直觉就能正确判断对方的意图,采取“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应对策略,最终大体上维护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社会正义。
(作者:郑磊 编辑:董明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