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施诗 上海报道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如今,距离中国入世已经过去二十年。入世20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与世界实现了共赢。与此同时,国际经济格局也不断地改变。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WTO亟需一场改革。
对此,瑞士日内瓦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高级经济学家Richard Baldwin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WTO应该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一样,需要改变组织的目标,应该从“我们拒绝(We say no)”转变为帮助人类应对各类已知和未知的挑战。“国际贸易体系最终将被视为人类在面对疫情时的救星。”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全球化面临各种挑战。Baldwin向记者表示,逆全球化并未发生,只是在工业制成品和服务业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转化。“数字化削弱了商品贸易的重要性而加强了服务贸易的重要性。”
Baldwin还向记者强调,尽管当前区域合作日益增多,但是全球贸易规则基石犹在,因此区域主义总体并不具有威胁性。“区域合作与多边主义是相辅相成的。”
WTO改革应注重帮助人类拯救生命
《南财对话》:在你看来,新冠疫情如何改变全球发展的轨迹?
Baldwin:新冠疫情带来了巨大冲击,但现在谈论结果还为时尚早。疫情几乎加剧了所有国家之间及国内的不平等。目前不断出现的变异病毒说明疫情距离结束还有很远的距离,因此疫情的影响仍难以判断,除非全球一起努力全面控制疫情。短期而言,疫情对全球化造成巨大冲击,但这也可能是一次全球合作的好机会。
我不知道疫情将走向何方,但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合作对解决疫情至关重要。疫情是我们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没人可以互相指责。这只是一次传染病。新冠病毒为人类带来了一次共同面对的挑战,在疫苗、医疗设施、供应链等方面携手合作的机会。这对于抗击疫情具有重要意义。
我认为WTO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在推动全球合作。我认为贸易体系最终将被视为人类在面对疫情时的救星,因此它的作用将得到强化。尽管目前各国在关税、补贴等问题上的意见不一,但我认为疫情有可能会帮助我们将WTO转化为帮助人类拯救生命的体系。
《南财对话》:我们都知道WTO需要一场革命。那么它的新方向是什么?
Baldwin:我认为WTO需要一个不同的心态。如今,WTO是一个“我们拒绝(We say no)”的组织,这导致鲜有双赢的成果。经济自由化会为各国带来共赢,但是“我们拒绝(We say no)”的心态令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重大进展及世贸组织成立所带来的积极影响都逐渐消失,而目前快速增长的贸易并非真正的全球化。
事实上,WTO的目标并不是绝对明确的。我认为WTO需要改变其使命,将目标转移到拯救人类、鼓励气候变化方合作等方面。IMF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基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IMF成立于上世纪40年代,曾在很多方面提供了稳定性。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停止黄金兑付美元的行为摧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IMF不得不困中求变,将自己重新塑造成“全球消防员”,帮助陷入困境的国家解决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
因此,我认为如果WTO要重振雄风,需要像IMF一样改变自己的目标。尽管WTO在维持基本贸易规则、创造透明的和非歧视的合作平台等方面仍保持重要的地位,但是为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承担更多的使命,WTO需要改变使命。WTO需要帮助人类应对诸如疾病、气候变化或尚不为人所知的全球挑战。
《南财对话》:你如何看待WTO的未来?
Baldwin: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在奥孔乔-伊韦阿拉的正确领导之下,WTO将把焦点从 "拒绝(Say no) "转向“我们可以拯救生命”。我认为这一个改变终将发生。我不做预测,但我很乐观。
数字技术不会完全取代人类
《南财对话》:在你的新书《失序:机器人时代与全球大变革》中,你创造了一个词“全球化机器人(globotics)”。这个单词有何意义?
Baldwin:“全球化机器人”是由全球化和机器人技术合成的新词。尽管大多数人将全球化与机器人技术视为两种不同的事物,但是我认为数字技术其实正以相同的速度推动二者发展,都将对工作造成冲击。因此,当我们考虑未来的工作和全球化时,应同时考虑自动化与全球化的影响。
《南财对话》:与过去两次工业革命相比,数字化的区别是什么?
Baldwin:自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被广泛应用以来,数字化一直都在进行中。但与先前主要影响制造业不同的是,目前的数字化正在冲击着服务部门的工作,而不仅仅是制造业的工作。当前我们的思维框架和政府的大部分政策仍然局限于全球化正在影响制造业、采矿业或农业部门,仍然认为全球化主要影响的是商品货物流通。然而在未来,数字技术将使跨国远程工作成为可能,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化的性质及其所直接影响的人群。同时,数字技术赋能的机器人,或者说自动化软件,正如同过去25年里工业机器人取代工厂工作一样,取代一些服务行业的工作,如自动泊车、考勤、银行柜员或邮政等领域。
《南财对话》:人工智能会给就业市场带来哪些方面的压力?
Baldwin:我不认为数字技术正在取代工作,也并不认为数字技术变化全都是负面的。数字技术在取代部分工作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工作。但问题在于,这一切都在加速发生,就业市场相较于过去将受到更多的错位影响。
我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的问题是技术进步加速对服务业影响加剧,而服务业的工作相较于制造业而言更容易被替换。劳动者面临的不是失业,而是将被迫频繁更换工作以适应变化,从社会角度而言这将是痛苦而具有破坏性的,也要求政府采取相应政策来帮助劳动者。
《南财对话》:人工智能将在哪个行业中取代人类?
Baldwin:我认为制造业的替代已经是迫在眉睫,但人工智能永远不会完全取代人类。这就类似拖拉机完全革新了耕作,减少了农民数量需求,但拖拉机永远不会取代农民,因为农民仍然需要做某些非常人性化的事情,例如对道德的判断、创新、处理未知情况。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人工智能将改变工作生态,如酒店前台登记服务、银行出纳等,但这些变化不会完全取代人类。
目前人工智能对工作的影响还不甚明了,因为其进步速度非常快。在未来5到10年内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将是颠覆性的。但我认为预测未来5到10年内的变化已经足够艰难,这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至于更遥远的未来的变化,不妨交给科幻小说作家去考虑。
全球经济领域已是多极化世界
《南财对话》:你认为数字化将如何改变全球化?
Baldwin:数字化通过两种方式改变全球化。其一是通过制造业的自动化。这将人类从制造业中移除。对于制造业而言,生产成本最大差异即在劳动力成本中,当单位生产所需劳动力数量足够低的时候,生产将转为本地化,例如欧洲超市中贩售的新鲜面包,其生产所需劳动力极低,不值得集中生产然后通过物流分发。因此,我认为数字化将减少商品贸易,一切都将在当地生产、当地售卖。其二,数字技术正在使贸易和服务更加自由便捷,这也将使服务行业全球化。我预测未来全球化将从商品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众所周知,在过去至少十年中服务业增速领先于制造业,而我认为这个趋势将受制造业及商品贸易下降的影响而加速。
《南财对话》:你在书中也提到未来全球贸易将从“我们制造(What we make)”转变为“我们服务(What we do)”。能否详细阐述?
Baldwin:简而言之这个概念即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即“我们制造商品”转化为“我们提供服务”。这个说法只是为了促进公众关注和理解。中国的制造业工人比例较之其他国家而言非常高,但工人占总劳动力比例仍低于50%。换言之,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在从事服务业而非制造业。尽管目前是全球化的世界,但大多数服务行业从业者并未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他们从未直接参与和外国从业者的竞争及互动。
《南财对话》:你曾说我们正处于全球化4.0时代。那么多极化是否会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Baldwin:毫无疑问。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并且其占比仍在不断提升。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都是制造业大国。其中,中、美、德三国具有相当的领先优势。其实,历史在不断重演。美国在19世纪崛起时,权力中心从欧洲转移,最终美国崛起成为超越其他国家的强权。如今,伴随着中国国民收入快速上升,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确已经成为世界的一极。虽然目前印度国民依旧较穷,但是他们有13亿人口。如果在任何一个单独国家里把任何事物乘以13,这就会变得很重要。多极化的世界日益明显。
我认为可以将中国、美国及欧盟视作三个相对的、有凝聚力的经济治理区块,提供经济供需力量。姑且不论军事及地缘,在经济领域目前已经是多极化的世界。
《南财对话》:能否回顾下前三个全球化阶段?
Baldwin:目前我们正处在全球化4.0时代,数字化削弱了商品贸易的重要性而加强了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数字化的发展为海外转移劳动力及跨国远程提供劳动力服务解除了束缚,这在数字化时代以前是不可能实现的。
全球化3.0的时代,即从1990年左右到2016年。1990年左右的信息通讯技术进步为工业生产解除了地理束缚,技术进步允许生产者在远距离中协调生产进程,将生产阶段放在例如中国、墨西哥和波兰等国。工厂跨越国界改变了全球化的性质,此前货物信息等物的流动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的工厂里。然而在3.0阶段,货物、信息、服务、资本等在国际间流动。
二战后到1990年的阶段,是全球化2.0的阶段,该阶段主要集中在商品制成品贸易的双向贸易中,世界贸易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等国或者说在欧洲、北美或日本之间。
1820年到1918年是全球化1.0阶段。由于蒸汽及其他形式的机械动力的出现,购买异地商品变得更经济实惠。当时是由英国主导的贸易,即在一地生产然后在另一地区销售,销售的商品有着巨大差异。
一国优先不是发展的正确道路
《南财对话》:近年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关于逆全球化的讨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Baldwin:我认为就一部分而言,全球化基本上是一个神话。人们认为金融危机扼杀了全球化,指出贸易总额与全球GDP比重在2008年之后在下降,这种下降被视为逆全球化。但事实上,下降主要源自中美两国贸易占GDP比重的下降。此前中国的占比在2006年达到高峰后逐渐下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正常的巨型经济体。随着制造能力进步、市场规模扩大,中国贸易生产更多集中于国内,因此其贸易占GDP比率也开始和日本及美国趋同。美国的贸易与GDP之比则从2011年开始下降,因为美国贸易正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商品贸易没有上升但服务贸易在增长。如果将中美排除在外,全球其他地区比率仍在上升。
我认为逆全球化本质是区域性的,对中国而言其比重下降是经济正常化的结果,对美国而言则是从工业生产转向服务业的结果。我并不认为这是逆全球化,只是在工业制成品和服务业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转型变化。
《南财对话》:未来区域合作会不会取代全球化?
Baldwin:我认为区域合作和多边合作是完全互补的。过去,区域自由化比多边贸易自由化进行得更快。此前WTO的成立和乌拉圭回合谈判是多边贸易自由化的重要里程碑,但随后其进展缓慢,而区域合作则进展显著。各地区在生产贸易中有着不同的类型,例如东亚的零部件贸易及跨国生产,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密切贸易交流等。这些不同的贸易类型需要不同的经济治理方式,因此,我认为区域合作和多边合作是相辅相成的。当贸易自由化被嵌入多边体系时,区域自由化将是终极结果。
不过,如果没有全球规则,区域合作的发展可能会令人忧虑。由于条件不同,区域贸易协定与全球贸易协定有所差异。我认为目前全球贸易有良好的基本规范,尽管自2016年以来受到诸多挑战,其基石犹在。因此区域主义总体并不具有威胁性。
《南财对话》:假设你现在是国家高级决策者的顾问,会有哪些建议?
Baldwin:从高层次而言,我认为新冠疫情创造了一个时刻,让人类意识到人类是共通的。自私地思考每个国家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这不是真正正确的前进方式。孤立主义或者一国优先并不是正确的发展之路。
新冠唤起了全球公众对于全球和谐的诉求。某种意义上说,新冠疫情是一个完美的教学时刻,让人类明白全球和谐的意义。但抗击疫情不是终点,而是一次推进全球合作的机会,尝试推进全球合作以帮助人类应对在未来几十年可能面临的挑战,比如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也是迫在眉睫的挑战。
策划:于晓娜
监制:向秀芳 方晓茸
记者:施诗
编辑:李艳霞
制作:李群
拍摄:陈蓁
字幕:王梓涵(实习生)
海报设计:张乔乔(实习生)
新媒体统筹:丁青云 赖禧 丁海利 曾婷芳
出品: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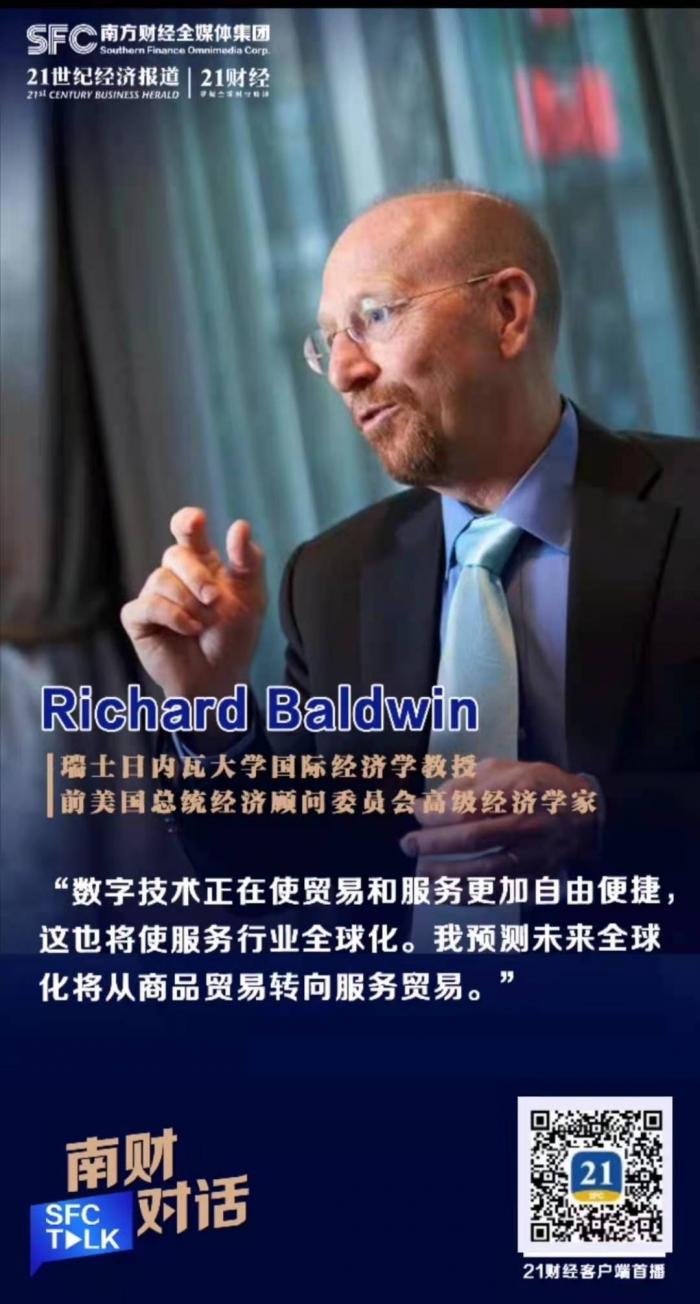
(作者:施诗 编辑:李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