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磊
人类的大脑结构和思维方式是进化的产物。有关概率的理论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尽管人类并不擅长思考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也并没有影响在不确定环境中的正常生活。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这个现象。《极端不确定性》用大量社会科学实例,结合数学、心理学、历史等多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给出了提高认知和决策能力的科学方法。作者讨论了主流经济学模型可以描述的“小世界”,和充斥着人类有限理性行为的现实世界(大世界)的差别。前者是确定或随机的,但是选项和概率是可知的,而后者则是一个极端不确定的世界,人们无法获得全部所需信息,甚至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更无法确定发生的可能性有多高。用“小世界”的理论无法解释“大世界”发生的事情,这种尴尬处境推动了行为经济学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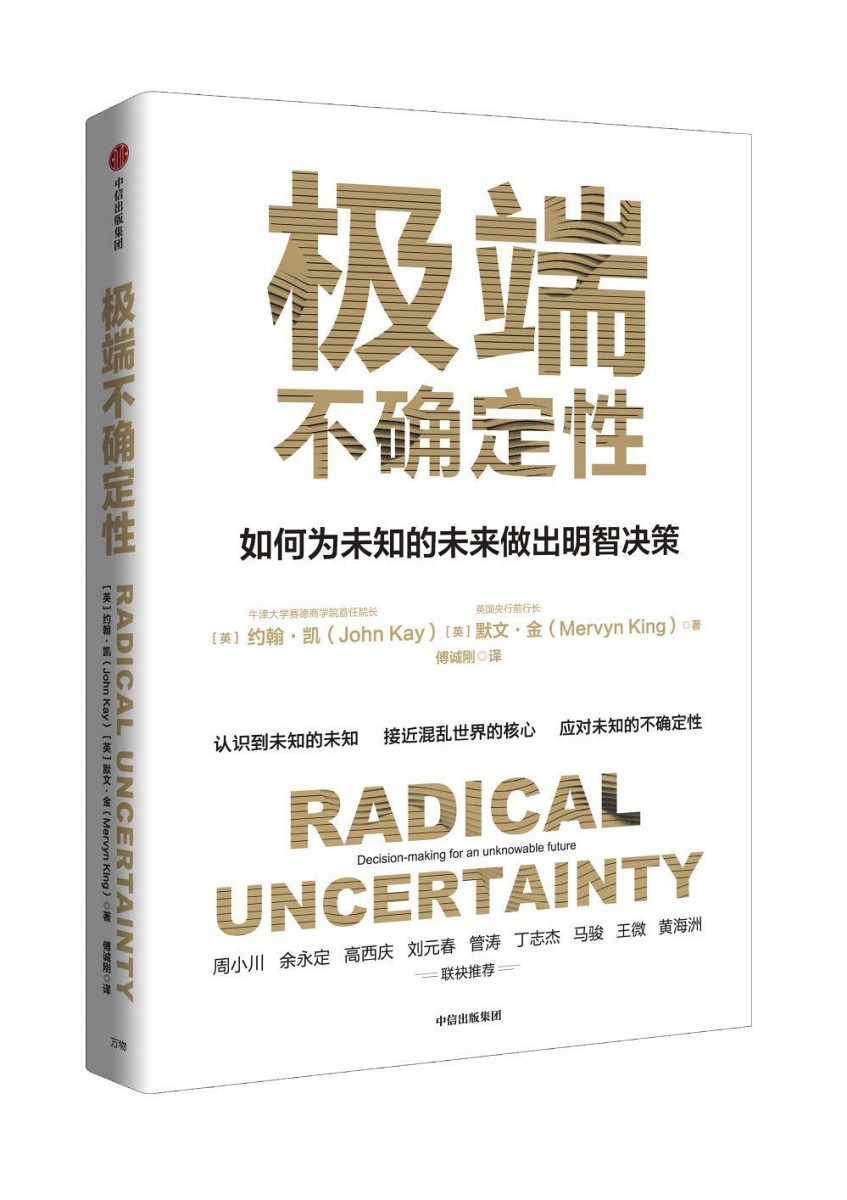
作者对利他行为的存在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在血缘关系之外,从基因角度看,相互合作的种群有更大的存活机会,使得与人为善、相互帮助的人群不断繁衍,成为族群的社会性规范或行为准则。从经济学角度也能推导出利他行为能够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一个间接证据是对“你认为可以信任大多数人吗?”给出确定答复的人越多,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也越高。利他使得族群规模不断扩大,风险管理成本降低,也有助于鼓励创新和劳动分工,这两者正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个人是自利的,但是从家族或更大的共同生活群体角度出发,有利于群体的行为特征却是“利他”。因此,人类行为结合了自利和利他取向,是自利的同时兼顾利他,甚至为了更高的目标,必要时能够牺牲一些个人利益。社会建立的道德规范和宗教习俗等各种机制也起到了遏制不合作行为、惩罚不合作个人的作用。
在行为经济学中,有学者提出每个人的价值评估其实包含了三个方面,首先是实用性,这方面与主流经济学类似,一般可以用经济变量表示和测量,比如货币收益。其他两个方面分别是表达性和情绪性的价值,前者比如可以带来社会声望、名誉上的好处(或者避免因违反社会规范而受到谴责),后者如会让自己感觉到开心快乐等。我们很容易想到,自利行为往往可以给个人带来实用和情绪方面的好处,但未必具有正面的表达性价值,而利他行为有可能正好相反。每个人其实可以在具体情境下综合考虑,得出一个总体上更好的选择。
无论对于博弈时的决策,还是单纯地做出选择,情境无疑是必不可少的。作者认为行为经济学采用的实验方法在这方面存在缺点,即实验人很少在给受试者提供必要的情境信息的情况下,要求必须在所给的选项中做出选择。笔者也有类似经验,经常会有受试者对问题和选项提出质疑,认为题目给出的信息不足以让他们做出选择,或认为提供的选项不充分,而觉得无法回答。笔者发现即便这些人为设计的问题和选项缺乏充分的背景介绍,人们总是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或习惯进行解读。当参与实验的人具有接近的社会背景时,他们的选择或行为是可以预测的。
行为经济学以理性人作为参照物,研究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思维方式的各种“不足”,其实就是经验方法的“偏差”。作者不赞同这种观点。既然常人无法及时获取完整信息并像电脑程序那样计算各种选择的利弊,然后做出精确的比较和选择,那么人类经过百万年进化而形成的思维方法,显然不应该被视为错误。基于完全信息和理性假设下的最优选择,极有可能让我们得到“精确的”错误结果,远不如人们基于经验去探索和寻找一个“模糊的”正确结果。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加里·克莱因所说:“对于有经验的决策者来说,决策重点在于如何评估当下的情形,回忆类似的经验,而不在于比较不同的选择。”这个概括有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即人类决策的前提是丰富的经验(或知识)。这与我们观察到的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人往往能力较强的现象是相符的。
当然,所有经验方法都有缺陷,行为经济学和认知心理学指出了人们在使用经验方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比如偏向根据手头容易得到的信息做判断,过度自信,有选择地过滤信息等。一个简单却不容易实行的方法是借助众人的知识和经验,尽量避免个人偏见或知识、经验的盲区。这需要置身于极端不确定的“大世界”的我们必须保持开放心态和冷静头脑,在做出决定之前,尽可能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要慎重思考与自己不同的异见。(作者系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编辑:杜尚别)